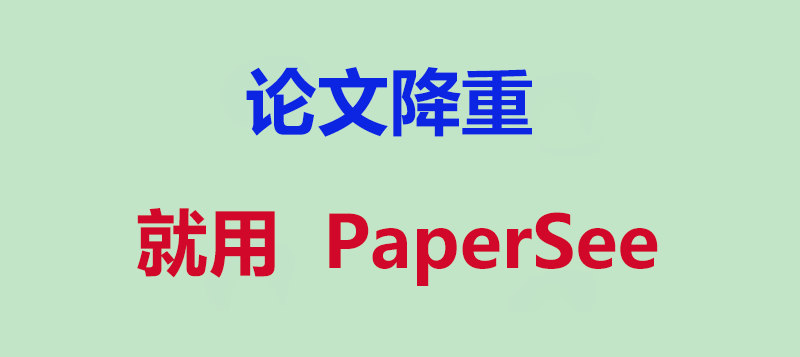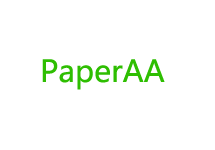小编: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在推荐岳雯作品入选中国作协的世纪丛书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岳雯是个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才情、天分、勤奋,使她在所经营领地里已经焕发出了与自
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在推荐岳雯作品入选中国作协的21世纪丛书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岳雯是个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才情、天分、勤奋,使她在所经营领地里已经焕发出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光彩——当然是指已经大大都超出了大家预期。
岳雯在我尚未成为她同事的时候,就已让我刮目相看了——她的文字灵动、坚实、饱满,2012之《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在我眼里是才气未可限量的巨大表征。
她目前的主要领域是小说评论,其实她本来就有治文论、美学之类的积累,理论功底从批评文字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觉得,长篇小说只是她由于“盘点”而顺延的职责之一,任何文学形式,都可以在她手里或笔下有声有色。
这缘于岳雯对文学格外之强的理解能力,文学在她眼里是个鲜活的存在,不是可以用条文来规定的,不是可以用概念来规范的,她拒绝教条的框定,与成规保持距离,使自己眼中的文学世界拥有了开阔的生成可能性。
“整合”与“拆分”是大多数评论者要做的,岳雯也不例外,但在她手里,这些事情与文本所指是无缝的,聚还是散、留还是弃,仿佛都在她的指掌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这就要说到悟性,热爱是极好的老师,但没有悟性,热爱会导致蛮干、平面化或者还有扭曲,岳雯的悟性当然是天生的,但她对书、对文字的喜爱,对“好东西”的天然亲和,能够保证她早早地站在一个结实的地方。
评论者立得住要在思维方式上过硬,岳雯这方面有天生的灵气。
还有,评论者的人缘儿相当程度上说要靠文字,如果文字上获得不了自信,就永远是心虚的。岳雯的文字固然有女性“妖娆”的一面,但准、精、丰富是带更根本意义的。
在我们创研部这个集体里,岳雯的工作业绩同样说明了她的干练、多能——那种独立地、恰当地、高效地完成任何指令的能力。
岳雯是个正在发出光亮的“星”,当然属于21世纪及以后。
到目前为止,岳雯尚未出版过个人文学专集。
我向大家隆重而严肃地推荐她的入选。
推荐语写到这个份上,按说不该再说什么了,再说就絮叨了。况且,在后来的评审会上,她的得票情况,也说明了大家都没看走眼。但回过头来再读读她的那些文字,总觉得还应说点什么,作为序,也有些话是需要补充的。
其中有一点想说的,是岳雯思维的连续与延展性。我们在读不少评论时会发现,作者的写作实际上是在那里挤牙膏呢,一会儿一截,一会儿一截,粗细一样了,长短透露出来的节奏却是不同的——关键是中间隔着一大截子,凸显出话语的滞涩、艰涩或勉强,这难道不是思维延展性不强的表现吗?我想是的,说明下笔时作者并未想得很明白,而岳雯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毛病。她思维的连贯性、通畅性令人惊讶,她的“思维点”总是能够被生发到当止之处,如种子一旦萌发,她能够保证其破土后的坚实,以及随后生长的顽强、茁壮。如回顾2013年长篇小说的那篇文字,似乎是由《带灯》去结构文章的,其实也不一定如此,反正开头是《带灯》,结尾还是《带灯》,她的流畅,她的把控能力,说明评论在她那里不是技痒的冲动,而是在有所发现与洞见之后,善于对自己找到的意识、观念、态度进行反复的加固与肯定。
还有一点,就是岳雯的文字里所隐含的个性与共性。评论是文字造就的,衡量文字的优劣,其中一个尺度,是要看能否充分表现个人性格、眼光、学识等等,或者让人窥见其气质的特色。那些经不起推敲、咀嚼,那些不够成熟的文字,往往建立在过于共通、过于大路货的语言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词汇的贫乏及句式的单调,而好的文字则是个性化的、鲜活的,而且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个性的建立断然离不开传统的承继、谱系的延续,否则我们认不出文字的来路、思想的累积,即使“野狐禅”也是有所本的,但出色评论家的语言必须出于传统,却能超越传统的共性,也就是要有“个人的声音”,如宇文所安所说:“一个有着个人的声音的作者可能渴望以集体的声音言说,我们觉察并欣赏他内心的这种冲动,但它仍不过是个人的、复杂的、不安分的版本。”(《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建立个性与突破共性的局限性,特别是克服“共通性”,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结果会是新天地的打开。
再有一点想说的,是岳雯在言说资源之左右逢源方面的出色表现。其实做个评论者挺冤的,成天要面对和思量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相识或不相识的作家、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种种文学现象,本来是要当个茶足饭饱之后的欣赏者的,却没料到不这么简单。不知不觉中,常常发现自己做着有点像桥梁、人梯、推手一样的事情,类似赏而不欣、知赏而退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赏而不欣”,是否还要说些什么?答案是“一定”。如果“知赏而退”,能够保持沉默吗?回答是,往往“并不可以”。评论家有时并没有沉默的特权,个人喜好也受到了局限,这是由职业伦理或专业规定性所决定的。同时,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作品,我们沉醉于阅读带来的狂喜的时候,你真的能够表达得出来吗?真的有言说的足够、独特依凭吗?这时,作为一个职业致力于“挑选、界定和敞开”的人,考验才真正开始,我无意于断言岳雯在掌握言说资源方面达到什么境界了,但她走过的路给了大家一种证实——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论,还是西方的新锐观点,抑或别的什么类似“批评观”的依托,反正岳雯似乎开始进入游刃有余的境地了。她有滔滔不绝的语流也好,她表述时的独特性也罢,都是很好的表征。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岳雯恰在这时开始提醒自己不要说得过多,她说:“关于文学,那些深处的那个我,仍然是沉默的。”
也许,我们都该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6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