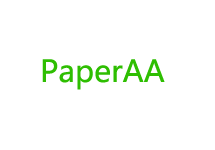以赛亚的第三个圈子:上流社会。起初是英国的上流社会,但很快扩展了出去。晚年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有567个人,我全认识他们”。然而,他作为观察家已经够讽刺的了,不能再说他是一个“势利者”,“势利”在文中似乎是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词。他拥有无法餍足的欲望和能力(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已经很明显),认识非常广泛的人群,尤其是政治界、外交界、文学界(斯蒂芬·斯彭德是他早期认识的重要的终身朋友,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是经常联系的人)、新闻界、音乐界、当然还有学术界的人。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似乎真的认识——或者已经认识——“所有人”。这得益于某种交谈变色龙的品质(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意每位对话者的观点,通过慷慨地认同来取悦他们,然后再加一点自己的想法。在描述两位哲学家和一名女子的紧张三角恋时,他自嘲说:“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微妙、机智地充当全世界的朋友。”在他的晚年,我有时觉得他将它提升成了实用的原则:为了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快乐,采用变色龙主义是合情合理的。小编:以赛亚的第三个圈子:上流社会。起初是英国的上流社会,但很快扩展了出去。晚年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有个人,我全认识他们”。然而,他作为观察家已经够讽刺的了,不能再说他
在这些20世纪30年代的信中,他是一个机智的社会观察者,写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话:“理查德·克罗斯曼正在试图再次出卖自己的灵魂,但连在那些认为他有灵魂的人当中也找不到买家”;指导本科生“就像在肥皂上点火柴”;“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还是跑进跑出,发出的声响就像带着一笼母鸡穿过田野”。他的信大谈早已不复存在的各类“明星”和“有点邪恶躯体味道的社会”,还采用有意强调和有点聪明年轻人的风格叙述,这有时令人厌倦。万灵学院的全称是“忠实逝者的万灵学院”(The College of All Souls of the Faithful Departed),但有时它感觉是“不成熟逝者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of the Frivolous Departed)。正如他在一封写给伊丽莎白·鲍恩的信的结尾自嘲所说:“这里面可能有许多戏剧性的废话,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重读这些信。”
我们没有听说太多有关他追求知识的东西,或许这并不令人吃惊,不过可以看到每周四他与弗雷迪·艾耶尔(A. J. Freddie Ayer)、奥斯丁(J. L. Austin)、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进行哲学座谈会时极其兴奋的状态,以及与斯蒂芬·斯彭德的一些惬意的文学交流。1935年,在万灵学院写给斯彭德的一封信中,他评论了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及其1900年的著作《生活的挂毯》(Der Teppich des Lebens):
我觉得你对格奥尔格的评价很对。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诗人,有时“生活的挂毯”华丽无比,其他书中的古怪东西也是一样:至于你引用的段落,我认为他是一个迫害自大狂,他最亲密追随者的任何辩护都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他是一个有着令人厌恶的看法或实际生活模式的人,他毁掉了自己的许多朋友,剥削他们,利用他们,等等,就像瓦格纳(Wagner)有时所做的一样,不仅像乔治·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烧死他们,或者像劳伦斯有时肯定会做的那样折磨他们(这是不是废话?),还冷漠地利用他们,不是凭借他的本性而是凭借他自认为的身份,或者至少说是凭借他决定发挥的作用。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扰中,欧洲政治受到的威胁相对那么少。1931年,在一次与斯蒂芬·斯彭德一起去萨尔茨堡音乐节最早的每年定期旅行中,他记下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纳粹党人——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穿着官方的褐色制服,在他的袖子上有一个红黑色的卐字,戴着小小的黑羔皮帽,帽子上还绣着银色的标记”。1933年去了罗塞尼亚(Ruthenia):“五种主要语言、七种次要语言、四条边境线、美丽又疯狂的犹太人、小气的乌克兰争吵者。”在万灵学院的晚餐桌上,回响着安抚希特勒的争论声。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牛津大学的德国贵族,后来因参与抵制希特勒被处死——在柏林圈内进进出出。但是,关于分崩离析的欧洲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听到的东西就像从学院高墙另一边繁忙大街上传来的回声。
这可能刚好部分反映出以赛亚认为适合写信的内容,又刚好这些信件幸存了下来,传到了他的传记作家亨利·哈代的手中,哈代呼吁所有拥有其他信件的人将信拿出来并开始编辑该书。实际上,为了恰当地阅读该书,你还需要有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关于以赛亚撰写的优秀传记。[145]在其他情况下,以赛亚可能仍然只不过是牛津的一个伟大人物,是当地的传奇但并不是一个拥有更广泛重要性的人物,就像他之前的榜样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一样,伊格纳季耶夫称,伯林著名的声音和风格就是模仿莫里斯·博拉的,然而,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让他免受这样的命运、让他成为本国和国际重要思想家的是他的更广泛的三个生活圈子:他的犹太联系,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巴勒斯坦以及后来以色列的关系;美国(1940年他去了美国);俄国。
对于我来说,该书披露出了1934年以赛亚首次巴勒斯坦之旅惊心动魄的生活。显然,以赛亚深知自己是犹太人,但人们可以在文中看到,他一边被完全接受为英国社会聪明的年轻成员,一边他还是被清楚地定义为“犹太人”。在新学院的晚宴上见到他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对她的外甥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写道:“有伟大的以赛亚·伯林,从相貌来看是葡萄牙裔犹太人;牛津大学的重要人物;我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吞火者。”
现在,在巴勒斯坦,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如果不是直接冲突的话,也是处于紧张关系中。他与他父母的俄裔犹太朋友伊扎克(Yitzchok)和艾达·沙穆诺夫(Ida Samunov)一起住在耶路撒冷乔治国王大道的潘森·罗姆酒店(Pension Romm),而他的旅游同伴、万灵学院的非犹太研究员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下榻在更豪华的大卫王酒店。以赛亚在一封信中对他的父母解释说:“那里有些麻烦,所有犹太员工都被突然开除了——劳动力的问题——因此现在犹太人待在那儿不太受欢迎。”一位儿时的犹太朋友非法在“一家巴勒斯坦的报纸”工作。但“今晚我和福斯特与许多年轻的(英国)官员吃饭。伊扎克想要我‘教育’他们。这个我不会做”。
他一下子在殖民政府里与牛津的同时代人、朋友坐在一起,一下子又与一位觉得受到可怕压迫的犹太家庭的朋友坐在一起。他对自己的父母写道:“然而,气氛虽然紧张但美妙:犹太人。到处都是犹太人。假期的时候,你可以轻松一下:许多希伯来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的郊区唱着俗气的歌,但唱得不是很响,人们在塔尔西姆(Talésim)闲逛等。”然而,“犹太人的观点与英国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关于一般政策的东西比关于小小的粗鲁、野蛮和侮辱的东西少。”他还补充说,“英国人是C3”——指低级的。他给马里昂(Marion)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写道,巴勒斯坦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共学校的人——低下的群体——充当的”。“至于犹太人,他们最不寻常又最迷人,我对他们同样感到不自在,避开他们。”
有点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英国自称是“Metic”——这是一个古希腊词,指住在希腊城的外来人,拥有一定的而不是所有的公民权。正是这种外国性、临界距离、从未有相当完全自在的感觉,让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提高。通常,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在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异化。所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都是Metic。比如说伯林,他价值多元主义的核心哲学观点起源于这种经历和紧张关系,这样假设似乎是公平的。
伯林在美国的五年多岁月(这占到了该书近一半的篇幅)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发生了——因为他试图去俄国。到了1940年的夏天,他的大多数英国朋友要么在军队,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哈代表示,以赛亚因出生时受伤,左臂无力,无法参军,又因为他是外国血统,无法进入政府部门。他沮丧不已,给时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写了一封信,想在俄国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文化—政治情报站服务并担任英国的调查员(“只听到我说话的俄国人根本不会认为我是外国人”)。该信似乎不是以这种形式发送的,但或许是以相似形式发送的。
大概在同一时间,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拜访了他,当时伯吉斯是以品行不端、醉酒闻名的英国外交官,但事实上他是一名苏联特工。伯吉斯建议伯林做英国媒体驻莫斯科的随从,他(伯吉斯)应该陪他先到美国获取必要的苏联文件,然后再去莫斯科。伯吉斯可能觉得以赛亚是他向其秘密苏联上峰回报的有用掩护。哈利法克斯勋爵随后很快签署了旅游护照,要求“让以赛亚·伯林先生通过美国和日本自由地进入莫斯科”。
当时,以赛亚有点契诃夫的样子,在华盛顿闲坐叹息着“要去莫斯科!”,而他不知道的是,约翰·福斯特敦促政府加以阻止后,只有正在旅行的外交官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心急如焚,但实际上巧妙地阻止了伯吉斯不同寻常的计划。(亨利·哈代精心重建了这个故事。)幸运的是,后来英国情报部门和大使馆发现了他的才能。他的任务是报道和试图影响美国的犹太社区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影响他们就是让他们更同情英国对抗希特勒的事业,当时,美国没有参与。他在纽约愉快地向父母写道:“这里的犹太人很难对付,但我希望应对他们,让国王陛下的政府受益。”然而,他同样善于认识新政华盛顿政府(New Deal Washington)的上层阶级,比如艾尔索普兄弟(Alsop brothers)、菲利普(Philip)和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他交朋友的天赋有了很好的发挥余地。
以赛亚从纽约和华盛顿发回来的报道非常丰富生动,甚至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还带来了一个著名的片段,当时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146]应邀出席克莱门汀·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的午宴,接着英国首相开始嘲讽美国的政治,误以为自己在与写那些非凡报道的以赛亚·伯林聊天。
哈代在此收入了一个以赛亚报道天赋的例子——一份“美国人对英国人有偏见的东西”的名单,包括从帝国主义、阶级制度到“英国人说话不爽快”,不一而足。在美国的英国人用谨慎和保守代替了圆滑,不允许自己强烈同意或者不同意美国说话者的观点,但想说这“非常有趣”。英国外交官将这份名单传给了伦敦的外交部,他将其作者形容成“在英国驻美宣传部工作的非常聪明的犹太人。这个文件能够让人感受到该犹太人的幸灾乐祸,他发现另一个种族(哈代在这里加了‘原文如此’)也不讨人喜欢——但它是相当高明的,大约有60%的内容是准确的”。
与此同时,私下里,以赛亚坦言非常思念英格兰。(与许多他那一代的英国作家一样,以赛亚互换使用“英国”和“英格兰”,但“英格兰”承载着更多积极的情感。)1940年8月,他在纽约给父母写信说:“英格兰要美丽得多啊。”六个月后,“我希望能在英格兰”。特别是纽约,他发现很难接受。他后来有些夸张地回忆说:
我过去常常站在洛克菲勒大厦(Rockefeller Building)的第44层,往下面的大街看,有某种想自杀的冲动。那些乱爬的小蚂蚁,多一只,少一只,根本没有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无用的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个性。在华盛顿,我的感觉相当不同。
他努力向总是充满爱意、关心有加、忧心忡忡的父母隐瞒这种更深的不满。他总是给他们发电报说:“身体很好。”(因此,书信集的英国版标题就是“身体很好”,遗憾的是,美国版的标题没有用它)甚至“请建议把伯林当作身体很好的同义词”。然而,有一次,他被迫承认:“我必须承认,像昨天我所做的那样在电报里告诉你我‘身体很好’并不是非常明智或者真实,那是夸张的。”他在纽约医院里写了这封信,当时他得了肺炎,正在慢慢康复。然而,当时,他还总结说:“我的身体基本上没问题。”
论文查重软件 论文查重免费入口 论文查重免费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8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