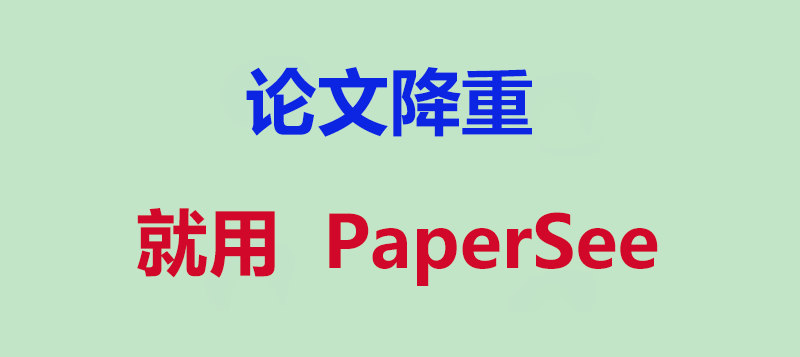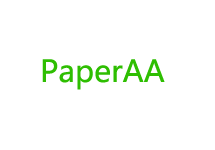小编:《安魂》:找寻精神出路的悲壮之旅我们每个人都惧怕死亡的降临,尽量在想象的世界中回避死亡的实在性。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其《文学体验导引》中说过,我们不愿把
《安魂》:找寻精神出路的悲壮之旅
我们每个人都惧怕死亡的降临,尽量在想象的世界中回避死亡的实在性。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其《文学体验导引》中说过,我们不愿把死亡如何降临与自己发生实实在在的关联,而且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文学趋于鼓励我们的逃避”,但他同时又指出,一些作家正如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所表现的那样,“没有试图令我们与自己的消亡达成和解,他也不想掩饰垂死的可怕之态。”(《文学体验导引》,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4页)也许,这样的艺术表现更有力量,更能深层次地接触到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无常,但托尔斯泰描写的是自己没有亲历过的死亡,是跨越了时空距离的人的生命的消失,也许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而所有这一切,对周大新来说,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周大新在壮年当了一次发生于自己家庭的可怕死亡的亲历者,现在,他要以这样的身份写作,记录下这可怕的过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不少人来说,其生命的延续往往也只有一次。正是周大新自己的独生子周宁,在踏上人生最美好旅程的时候,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周大新以自己的泣血之作《安魂》,对这一天塌地陷般的巨大悲惨事变做了一次直面惨淡人生的记录。
文学可以充当亲历者的实录工具,可以疗救人的心灵创伤,但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似乎向来缺乏直面人生惨淡、直面人生痛苦、直面人生难题的切肤之作。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讲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自己讳,不少人倾向于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封闭起来,习惯于多向外人展示自己的光鲜亮丽、成就功德,大家不约而同地尽量避免讲自己的短处、劣势,当然,大多数人更不愿在写作中触碰自己的痛苦、不幸与背运。而周大新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许,他长久以来就想走出这一步——痛快淋漓地向世界、向自己逝去的儿子说些什么,与自己经历的痛苦告别,与往事干杯,我们得承认,这是很了不起的壮举。
我们知道,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都是痛彻心扉的、无奈得难以想象的经历。生命之珍贵在于只有一次,上天从自己手里夺去意气风发的年轻儿子,无疑等于夺去周大新自己的生命,周大新作为一位敏感、智性的作家,恰恰经历了这么一个可怕而令人沮丧的惨痛事件,我们想知道他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曾用在对挽救孩子生命上的努力,想为他分担却终究还是没有留住孩子的遗憾,但我们没有指望他会这样做。现在,当一切都过去几年之后,他以一部潜心创作的长篇《安魂》,把所经历的一切向我们做了一次令人肃然起敬的倾诉。
他不想有任何掩饰地描写了死亡逼近的所有“可怕之态”,不管这个可怕之态如何令人恐惧、不堪回首,他都没有顾忌,他采用了彻头彻尾的写实手法,把“可怕之态”的所有细枝末节,做了几乎是不差分毫的还原——从儿子晕倒在剧场,到确诊患脑瘤,走上求医之路,从第一次手术治愈,到病魔再次无情复发,从寄托于《心经》,到走到生命尽头,周大新都没有回避、粉饰,也没有遗漏,他原原本本地为我们逐一做了交代、陈述。
这是一次撕肝裂胆的写作,是一次苦大恨深的告白,作家把疾病的狰狞做了全方位的告白、控诉,他让人们了解到病魔的猖獗,让我们再次直观生命的脆弱,让我们了解到命运之手如何置我们于无奈的境地。作品也形象地告诉人们: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会不知不觉地溜走,在需要我们倾心珍惜的时候,上天也许并不想给你机会。这个机会的可贵、无常让我们无奈。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生命的出色、为人生的完整付出自己的一切,毕竟,生命是一切的一切。
人类是时时需要为自己的情感、灵魂里的不安分找寻借口与出口的,从诸多方面讲,周大新创作《安魂》就是要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出口,因为,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老天偏偏向自己的儿子、向自己的家庭痛下了毒手。我们中国人的因果观念根深蒂固,我们面对灾难,总是倾向于从因果报应中找寻答案,想问老天一个究竟。而对周大新而言,无论是他的过往经历,还是他的为人处世,根本就找不到所谓“因果”的由头。在周大新那里,所有“为什么”都是一个个彻头彻尾的无解。王蒙先生在谈及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时说:“当人们不能够用逻辑、用知识、用学问来解释死亡的时候,还可以用艺术、用精神的向上升华和逼近的情感,来体验一下死亡对人生的意义。用艺术用交响乐来解释死亡、来探讨死亡,应该说这也是人们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出路。”(《老子十八讲》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8—169页)周大新的写作,无异于给自己痛痛快快找一条精神解脱之路。
同时我们也得承认,这是一部超越之书,是一次作家超越痛苦、超越自我,直面人生的磨难、勇敢地抗击命运捉弄的努力,但也决然不是一部艺术上不想讲究的率意之作,恰恰相反,这是一部精心之作,作家在文体上进行了极为大胆的实验和探索。作品总的特点是实现了纪实与幻想的杂糅、有机结合。作品前三分之一为回顾性记叙,实录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而在后面则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虚构了儿子在天国生活的状况,特别是虚构了儿子与从爱因斯坦到袁世凯、从伏尔泰到杨玉环等中外名人的接触、交谈,“人在生活中喜欢彼此比较,那可能是天性使然,是人自爱的一种表现,人在彼此的比较中要么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要么获得一种向前奋斗的动力。
当然,这种比较可能会带来痛苦,可能会带来绝望,可试想一想,倘若人们都不再相互比较,那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必定会成死水一潭,各种创造都不会出现,社会就会停止发展。”(第276页)作品通篇采取父子分述、父子对话的方式来结构,从不同的维度上丰富作品的内涵,其实也在不停地开辟表达、折射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对话、沉思、独语、反省、沉吟,从人界到冥界,他细细记录;从人间到天堂,他苦苦追问。他陷入无解的无奈,但他没有,也不会放弃探求。在万般的痛苦叙事中,在痛定思痛的虚构中,作者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经历了人生大痛苦、大沮丧与大失意之后,作家依然感情真切地劝慰人们,鼓起前行的勇气——为了人生的丰硕与完满。
查重 自动降重 论文查重什么意思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