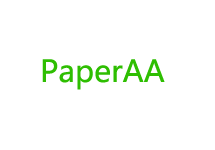2001年小编:年阿尔罕布拉“我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没错,我是西班牙。”诗人奥登()这样回应年的西班牙内战。六七十年后,西班牙成为另一场战争的舞台,这场战争影响每个欧洲人,所有
阿尔罕布拉
“我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没错,我是西班牙。”诗人奥登(W. H. Auden)这样回应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六七十年后,西班牙成为另一场战争的舞台,这场战争影响每个欧洲人,所有民主国家的每个公民。这是一场持枪的人和空中的人肉炸弹无法获胜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避免另一场战争的战争。
在马德里一条宽敞的城市街道一边,你可以在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Queen Sofia Art Centre)中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这或许是现代世界中描述战争的最著名的单一艺术画,这幅纪念西班牙内战期间遭轰炸小镇的画,用黑、灰和白三种分明的颜色描绘了扭曲和肢解的身体部位——腿、胳膊,大部分都是人头,每个人头都张着嘴,痛苦地嚎叫着。就在几米之外,街道的另一边就是阿托查(Atocha)火车站。2004年3月11日,在这里,格尔尼卡的一幕重演了。由于安在上下班列车上的炸弹的引爆,在短短几秒内,活生生的男男女女们——父母妻儿——的身体被撕成了一块块。我们肯定可以想象,他们还张着嘴发出最后一声痛苦的嚎叫。
毕加索并没有来纪念阿托查火车站的受害者。乍一看,纪念物可能是两台自助售票机。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装金属键盘的,你可以在键盘上打纪念或者表达团结的语句,它能与你手的扫描像连接在一起。在这两台记忆机器的中间悬挂着巨大的白色圆柱体,人们可以在这些上面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永远不要再发生”有好几处。“阿兹纳尔、布什和布莱尔是暗杀者。”还有不合语法的波兰乐观主义的动人心声:“不要继续深陷在绝望中。波兰。”
阿托查火车站的纪念物缺少艺术的壮观。然而,其极致的平庸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这场战争不会以某种大决战而是会以无数次日常的小小遭遇战(就像天天乘坐近郊列车上下班的人一样)的方式取胜或者输掉。
如果你往回走,从格尔尼卡博物馆到达拉瓦皮耶斯(Lavapiés)区,你便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许多北非移民都住在这里,好几个“3·11”爆炸案的制造者过去经常在这里出没。在特里布雷特大街(Tribulete Street)上,你可以看到小电话店(称为“展位”)闩着的铁门,移民可以在这里给家里打便宜的电话。但是这个展位的主人杰莫尔·左格姆(Jamal Zougam)利用自己电信方面的专业技能准备了几部手机,通过远程控制引爆了列车上的炸弹。现在他的房子已经用于出租,但是门上还有“新世纪展位”的图案。确实是新世纪了。
拉瓦皮耶斯区并不像是一个贫民区。在狭窄的街道上,西班牙和北非的商店仍然混在一起。人们也是一样。但我感觉这个社区可能向其中一个方向发展:要么加强和平共处,要么急速陷入低层次的城市内战。
或许西班牙人在“3·11”袭击后所做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回击,没有让任何国籍的摩纳哥人或者穆斯林当替罪羊。人权观察组织的最近报告谨慎地对此表示赞赏:“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记录在案的种族暴力事件可以直接归结于‘3·11’的爆炸事件。”该报告还援引西班牙摩纳哥工人和移民组织主席的话说:“所作出的反应总体而言可以作为楷模,这个社会知道如何区别少数恐怖分子和一个共同体。”
然而,与拉瓦皮耶斯区的人们交谈,你会发现一个接近引爆点的社会。一位西班牙的酒吧老板告诉我,他多么讨厌像他之前的邻居左格姆(手机操控炸弹的人)那样的人,颤抖的声音中透着愤怒和酒意。他说:“如果我3月11日那天有把枪,我会在这里自己打死他们。”穆罕默德·赛德是一名手上画着蛇的摩洛哥人,今年十九岁。他抱怨说,爆炸案后,警察对他们的骚扰越来越多。为什么,就在三天前,由于他朋友的手机中有一张奥萨马·本·拉登的照片,警察就打了他一顿并没收了他的手机!那么本·拉登是他这位朋友的英雄吗?没错,当然是。但赛德正在学做水管工,他说自己的老师对他一直很好。这么说,一个人正处在融合和疏远的风口浪尖。
我又问了一位能言善辩、十六岁的穆罕默德(“叫我穆罕默德就行了”),问他对去年发生在路那边阿托查火车站爆炸事件的看法。他说,他不想看到有人死掉,“即使他们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这次是因为阿兹纳尔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一切……
后来,在该市近郊一个戒备森严的会议中心,我在一次旨在讨论“民主、恐怖主义和安全”的纪念峰会上与一群杰出的政客、国际官员和思想家坐在一起。这次精心组织的会议的主题是“民主政府是抗击恐怖主义唯一合法并且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旨在一份马德里议程里制定在应对恐怖主义的民主回应中从未见过的最完整行动计划。
我期望研究结果。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显然至关重要,从协调的警察和情报工作到移民政策,从使更广泛中东民主化的竞争战略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正如两位穆罕默德的评论明确表示的那样,相应的政策会对我们自己阿拉伯的街道产生直接影响。
但是,如果欧洲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与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频繁的互动来有意识地参与这场战争,才能赢得这场避免更大战争的战争。这些体验将决定已经大量生活在我们当中的穆斯林移民是走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终走向恐怖主义,还是远离它。这不是“反恐战争”,在反恐战争中,强国强大的军队和安全设备屡屡被几个准备牺牲自己、技术精湛的人挫败。这是一场防止这类人想成为恐怖分子的战争。
一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就是“每天一次公民投票”。这场防止在普通男女遭疏远的脑海中出现恐怖主义的和平战争也是如此。这是一场应对小事、琐碎日常行为的战争。
回到特里布雷特大街上,有一家名为“阿尔罕布拉”的阿拉伯饭店,受到指控参与“3·11”爆炸事件的人过去经常来这里。我到那里的时候,遇到两名西班牙妇女正在学习阿拉伯语,熟悉他们邻国的文化。尽管她们是没有裹着头巾的西班牙妇女,她们也受到了阿拉伯饭店老板的热情招待。这,也体现了马德里议程。
2005年
欧洲的伊斯兰
2006年一个晴空万里的夏日,我参观了巴黎近郊著名的圣丹尼教堂。我欣赏了法兰克王国国王和王后壮观的坟墓和墓碑,包括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铁锤查理”)的坟墓和墓碑。人们普遍认为,公元733年,在普瓦捷附近,查理·马特击退穆斯林军队的入侵阻止了欧洲的伊斯兰化。(详见“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吗?”)走出教堂,我走了约100米穿过维克多·雨果广场便到了主商业街,街上到处都是阿拉伯和非洲裔的当地购物者,包括许多戴着头巾的女子。我突然想:这样看来穆斯林终究还是赢得了普瓦捷战役!不是靠武力取胜,而是靠和平的移民和繁衍后代。
从国王的教堂出来沿着道路往下走,在“一神论协会”(Tawhid association)不起眼的后院办公室里,我会见了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Abdelaziz Eljaouhari),他是摩纳哥柏柏尔移民的儿子,是一名口才出众的穆斯林政治活动人士。他用完美的法语流利又富有激情地讲述了巴黎周围贫穷住宅区的苦难——这正如我们所说又是抗议造成的——和对移民及其后代长期的社会歧视。他愤怒地说,法国所谓的“共和国模式”实际上是指“我说法语,叫让·丹尼尔,蓝眼睛,金发”。如果你叫阿卜杜拉齐兹,皮肤较黑,还是穆斯林,法兰西共和国就不像其所宣扬的那样做了。“我们有何平等可言?”他问道。“什么自由?什么博爱?”后来他给强硬的内政部长、继承雅克·希拉克的右翼主要总统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发了一封私信,信中的措辞我永远都忘不了。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大声说:“我,是法国人!”
此外,他可能还会补充说,欧洲人。严重疏远许多穆斯林人——尤其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那些自身出生在欧洲的年轻男女——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如果形势还像现在这样恶性发展,那么这种疏远和对主流白人、基督徒或者后基督徒欧洲人的怨恨互相推动的方式,可能会摧毁欧洲最牢固民主国家的公民网。它已经促进了民粹主义反移民政党的崛起,非常直接地导致了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穆罕默德·阿塔等劫机人员就是在欧洲期间被激进化的)、2004年马德里的“3·11”爆炸事件、2004年11月2日谋杀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梵高的事件、2005年7月7日的伦敦爆炸事件,还有2006年8月10日试图炸毁多架英国飞往美国的客机但被英国当局挫败的事件。
欧洲与其穆斯林之间的困境也是过度简单化的主题,在美国尤其如此,懦弱、反美、反犹太的“欧拉伯”(Eurabia)[55]这套固有思维,日益束缚着阿拉伯/伊斯兰占支配地位的地区,目前似乎正在加剧。作为欧拉伯的一份子,我必须坚持几点基本的区别。首先,我们是在谈论伊斯兰、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阿拉伯人、移民、皮肤较黑的人还是恐怖分子?这可是七种不同的东西。
在我住的地方——欧拉伯的牛津,我几乎每天都与大英博物馆联系。他们的家族血统源自巴基斯坦、印度或者孟加拉国。与我熟悉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相比,他们是更加和平、守法和勤劳的英国公民。正如一项有关法国伊斯兰的杰出新研究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法国穆斯林都相对较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56]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抱怨的歧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在着,对非穆斯林的移民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歧视。可以说,对皮肤较黑、用外国名字或有口音的人都同样歧视,这是赤裸裸的旧式种族主义或者仇外,而不是现在称为“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更加具体的偏见。
在欧洲大陆,对于伊斯兰,尽管有交叉的问题,但也有许多截然不同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有1400多万人口——至少占到其迅速减少的人口的10%——可以被认为是穆斯林,但是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他们不是欧洲问题的一部分。[57]相比之下,就拿土耳其来说,将近7000万穆斯林人居住在这个世俗国家,欧洲人激烈地辩论了这样一个主要是穆斯林的大国(在大多数传统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定义中,它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似乎应该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在巴尔干半岛,有数百年历史的欧洲穆斯林社区,总共有700多万人,包括基本上是穆斯林的国家阿尔巴尼亚、迟早穆斯林将占多数的另一个实体科索沃、穆斯林占多数的脆弱国家波斯尼亚和穆斯林占不少人口的马其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
这些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是老欧洲人,不是欧洲的移民。然而,像土耳其人一样,他们确实组成了德国、法国和荷兰等西欧国家穆斯林移民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在十年内,要么由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加入了欧盟,要么由于他们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获得了国籍,大多数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可能将成为欧盟的公民。20世纪90年代,西欧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迫害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回应虚弱无力(对克罗地亚的回应相对有力一些),令人耻辱,这加深了穆斯林在欧洲受伤害的更广泛认识。西欧人(和美国人)军事干预科索沃,防止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试图屠杀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常常就没有那么让人记忆深刻。
人们随意谈论“欧洲穆斯林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想到的是来自移民家庭的1500多万穆斯林,他们现在生活在欧洲西部、北部和南部欧盟成员国内,以及瑞士和挪威(生活在波兰等欧洲中部和东部欧盟新成员国内的数量很少)。法兰西共和国在理论上不管肤色、宗教和民族,但并没有真实的统计数据,这一事实使统计变得复杂,尽管如此,或许法国大概有500万穆斯林——超过总人口的8%。德国可能有400万人——主要是土耳其人,荷兰将近有10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5%。
其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一般在城市的特定区域,比如圣丹尼周围的行政区域,它包含了巴黎近郊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住宅区。每四个马赛市民中估计就有一个是穆斯林。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书《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Murder in Amsterdam)中,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引用了一份官方统计数据:1999年,阿姆斯特丹大约有45%的人口有外国血统,到201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上升至52%,其中大多数人是穆斯林。此外,穆斯林移民的出生率通常比欧洲“本地人”高。根据一项估计,十六岁至二十五岁的法国人口中穆斯林人超过15%。[58]
文章查重 知网查重 知网查重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7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