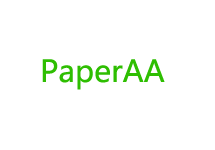反欧主义与反美主义并不对称。反美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怨恨夹杂着嫉妒,反欧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愤怒夹杂着蔑视。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ois Revel)所说,反美主义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困扰,对法国来说尤其如此。[75]反欧主义远未成为美国的困扰。实际上,美国对欧洲的主流态度是温和善意的漠不关心夹杂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知。我在堪萨斯州转了两天问我遇到的人,“如果我说‘欧洲’,你会想到什么?”许多人的反应是震惊和长时间的沉默,有时咯咯笑一下。接着他们会说一些“哦,我猜他们那边没有多少捕杀”(弗农·马斯库,马克洛斯的一名木匠);“呃,那离我们很远。”(理查德·苏扎,其父母来自法国和葡萄牙);或者,停下了思考很长一段时间后说,“呃,跨过池塘就是了”(杰克·维沙,一名有德国口音的老农)。如果你对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或者鲁塞尼亚(Ruthenia)最偏远村庄中的农民或者木匠说起“美国”,或许可以肯定,他有关这个主题可以说多得多的东西。小编:反欧主义与反美主义并不对称。反美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怨恨夹杂着嫉妒,反欧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愤怒夹杂着蔑视。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所说,反美主义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
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波士顿—华盛顿走廊”——我一再被告知,冷战后,连那些相当了解欧洲大陆的人也日益对欧洲漠不关心了。欧洲既没有被视为有力的盟友,也没有像中国一样被视为严肃的潜在对手。一位高中和大学都在英国读的美国朋友说:“它是老人之家。”正如保守派专家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交锋》谈话中所说:“谁关心欧洲人想什么。欧盟把所有时间花在了确保英国的大红肠用公斤还是用磅计价销售。整个大陆对于美国的利益日益无关紧要。”[76]当我向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询问,如果欧洲人继续从军力削弱的立场批评美国会发生什么时,他回答的大意是:“呃,这个重要吗?”
然而,我觉得这种漠不关心的说法也被夸大了。诚然,我的对话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告诉我他们是多么不关心。直言不讳批评欧洲的美国批评人士的本质是,他们通常并不是对欧洲一无所知或者漠不关心。他们了解欧洲——其中一半人似乎在牛津或者巴黎学习过——很快就提到他们的欧洲朋友。正如大多数批评美国的欧洲批评人士强烈否认他们反美(“不要误解我,我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一样,因此他们几乎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他们并不反欧。[77]
反美主义和反欧主义位于政治领域中相反的两端。欧洲的反美主义主要可以在左翼中找到,美国的反欧主义可以在右翼中找到。最直言不讳抨击欧洲的美国人是新保守人士,使用的攻击言论与他们通常抨击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一样。实际上,正如乔纳·戈德堡自己对我承认的那样,“欧洲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掩护者。因此,我问他,比尔·克林顿是欧洲人吗?戈德堡说:“是。或者说至少克林顿像欧洲人那样思考。”
有证据表明左右翼的区分也划分了公众的态度。2002年12月初,埃普索斯—里德民意调查集团在对美国民意的常规调查中专门为本文加入了几个问题。[78]要求他们在四种有关美国和欧洲对外交和战争的做法的说法中选择一种时,30%的民主党选民和只有6%的共和党选民选择“欧洲人似乎更喜欢外交解决方案,而不是战争,这是美国人可以学习的一个积极价值观”。相比之下,只有13%的民主党人却有35%的共和党人(最大的单一部分)选择“欧洲人过于愿意妥协,而不是为了捍卫自由不惜一战,这是消极的”。
当受访者被要求在有关“伊拉克战争应该采用哪种方式”的两种说法中选择一种时,情况更加泾渭分明。有59%的共和党人却只有33%的民主党人选择“美国必须继续控制所有行动,防止欧洲的盟友限制美国调兵遣将的空间”。相比之下,有55%的民主党人却只有34%的共和党人选择“美国必须与欧洲国家联合,即使它会限制美国做决定的能力”。实际上,确是共和党人来自火星,民主党人来自金星,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调查的假设。
对一些保守人士来说,国务院也是金星的前哨。美国世袭的新保守人士之一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写到了“一条和解之轴——从利雅得延伸到布鲁塞尔,再到雾谷(Foggy Bottom)”。[79]沿着波士顿—华盛顿走廊,我多次被告知,在伊拉克问题上,两派争着向布什总统献策:“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派”和“鲍威尔—布莱尔派”。英国公民相当惊奇地发现,我们的首相变成了美国国务院的高级成员。奉持大西洋主义的欧洲人不应从中获得过多安慰,因为即使在国务院毕生致力于自由的欧洲主义者当中,也有人对欧洲人失望了,尖刻地批评他们。他们失望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欧洲人没有在自己的后院阻止那场造成25万波斯尼亚穆斯林死亡的种族大屠杀。[80]自那以后,欧洲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因此连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就摩洛哥海岸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发生的争端也要由科林·鲍威尔来解决。
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在华盛顿一家酒店的正式早餐上对我说,“他们不严肃”是对“欧洲人”言简意赅的评判。尽管威尔根本算不上是国务院的一名自由主义者,但国务院中的许多人都认同该看法。真可谓历史轮流转,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年夏尔·戴高乐对美国人的评判是什么?——“不是很严肃。”
二
因此,在美国的很多地区,对欧洲失望,充满了愤怒,日益蔑视甚至仇视“欧洲人”,这在极端情况下称得上是“反欧主义”。为什么会这样?
已经出现一些可能的解释,全部拿来探讨需要写一本书。在此我只能讨论某些解释。首先,在美国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反欧洲主义。《大西洋月刊》的前任编辑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曾表示:“建立美国是为了对付欧洲。”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问道:“为什么要通过将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方的命运连在一起,让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幽默或者善变之中?”在19和20世纪,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欧洲就是一个要逃离的地方。
然而,对欧洲也始终有一种迷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就是著名的例子;从许多方面来说,渴望模仿进而超越最重要的两个欧洲国家——英国和法国。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引用了一句老话对我说:“当美国人死的时候,他们去巴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他的祖国和法国。”美国人对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变得如此截然不同是在什么时候?是1940年,法国“奇怪的战败”和英国“最美好的时光”那年吗?此后,戴高乐重拾法国的自尊,与美国人作对,而丘吉尔让自己父母的两个国家建立了“特殊关系”。(要理解如今希拉克和布莱尔对待美国的方式,关键人物还是戴高乐和丘吉尔。)
五十年来,从1941年到1991年,美国和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参加针对共同敌人的联合战争:首先是纳粹主义接着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这是地缘政治“西方”的鼎盛时期。当然,在冷战过程中也不断出现跨大西洋的紧张关系。人们可以发现如今的一些模式完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署巡航和“潘兴”导弹,以及美国对中美洲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对话中形成的。[81]它们是在相同的一些人心中形成的:比如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当时因其强硬的观点而被广泛称为“黑暗王子”。这些跨大西洋的争论通常是关于如何应对苏联的,但他们最终还是受到了明确的共同敌人的限制。
现在并非如此。因此,或许我们正在见证大约十年前澳大利亚作家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上所做的预言:这个明确的共同敌人的消失将导致作为牢固地缘政治轴心的“西方”的衰落。[82]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主要舞台,但它不是“反恐战争”的中心。相对实力的差距已经变得更大。美国不仅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这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即将相当于紧随其后的15个最强国家的军费之和。欧盟并没有将其可以比肩的经济力量——正在快速接近美国1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转化成可相颉颃的军事力量或者外交影响力。但不同之处还在于力量的使用。
罗伯特·卡根称,欧洲进入了“法治、跨国协商和合作”的康德式世界,而美国仍然处在霍布斯式世界,军事力量仍然是实现国际目标(即便是自由的目标)的关键。首要而明显的问题肯定是:是这样吗?我认为,卡根(虽然他承认那是“讽刺性的描述”)实际上对欧洲太客气了,他将欧洲的做法提升到了有意为之和有条不紊的程度,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胡乱寻求和国家差异的故事。但是第二个不那么明显的问题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希望是这样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相当多的美国决策者喜欢他们来自火星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这使他们崇尚武力(martial)而不是成为火星人(martian)——,而相当多的欧洲决策者喜欢认为自己确实是进步的金星人。因此,接受卡根的文章是其本身故事的一部分。
随着即将扩大的欧盟寻求更加明确的身份,将自己定义成美国的对立面对于欧洲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欧洲通过列出与美国的不同来清楚地表明自身形象。用身份研究的可怕术语来说,美国成了“对立面”。美国人不喜欢被“排斥”。(谁喜欢呢?)“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让他们更加愿意接受人们用崇尚武力和富有使命感来描述美国在世界的角色。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表示,法美两国都自认为肩负普世化、文明化的使命。现在出现了欧洲而不只是法国版的文明使命(跨国、以法律为基础的一体化的“欧盟乌托邦”),这与最近保守版的美国使命冲突得最厉害。[83]因此,比如,乔纳·戈德堡愤怒地引用德国大西洋主义老兵卡尔·凯泽(Karl Kaiser)的话表示:“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前所未有:创造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和平区域。欧洲人确信这个模式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效。”
双方各自认为自己的模式更好。这不仅适用于国际行为的竞争模式,还适用于那些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自由市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等的不同组合。[84]在《美国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一书的作者政治学家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看来,这预示着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文明冲突”即将到来。卡根认为欧洲长期虚弱,而库普乾认为欧洲而非中国是美国下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85]许多欧洲人喜欢相信库普乾的看法,但在美国,我发现库普乾的看法几乎无人支持。
我认为,在美国有另一种更深的趋势。我已经提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美国人对欧洲人的怀疑夹杂着羡慕和迷恋。直截了当地说,有一种美国文化低人一等的情结。这已经渐渐消退。到冷战结束和美国随后崛起为独特强国的时候,这种消退的速度已经以很难压制的方式加速。新罗马不在敬畏古希腊人。一位拥有丰富欧洲经验、退休的美国外交官最近写信对我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欧洲比我们优越。这不是个人方面的优越——即使屈尊于人,我也从不觉得低人一等——而是文明方面的优越。”现在不是这样了。他写道,美国“不再羞愧”。[86]
三
冷战结束后的八年里,名誉欧洲人比尔·克林顿掌管白宫让这些趋势变得有些模糊。2001年,乔治·W. 布什(对于所有欧洲反美讽刺漫画家来说是一件活生生的礼物)携带着一份单边议程入住白宫,准备拒绝多份国际协议。“9·11”事件后,他将自己的新总统职位定义为战争总统。我发现,“9·11”之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感觉在华盛顿比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其他地方都强烈。[87]最重要的是,它处在布什政府的中心位置挥之不去。“反恐战争”促进了共和党精英中现存的一种趋势,即相信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谓的“勇士政治”(Warrior Politics),这种政治具有很强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气息——这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显然是缺少的。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著作《特殊天意》(Special Providence)中所说,这将“杰克逊”的倾向重新带入了美国的外交政策。[88]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是新的克里克族印第安人(Creek Indians)。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