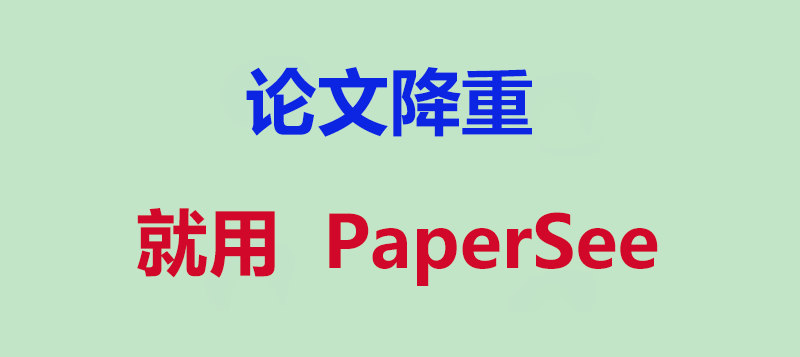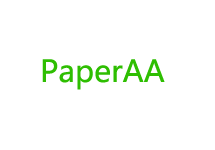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将平淡直白作为自己的写作原则,也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而独步美国文坛。小编: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将平淡直白作为自己的写作原则,也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而独步美国文坛。一次,他要到巴弗洛女子学院去作关于写作的报告。为此,他先认真审阅了该学院青
一次,他要到巴弗洛女子学院去作关于写作的报告。为此,他先认真审阅了该学院青年女子们写的文章,他在报告中指出两篇获奖文章的优点:“极少做作,极少雕琢,很清晰,很有条理而且很明白。”在总结获奖作品的可贵之处时,他说:“语言和主题不矫揉造作、简单明了,遣词造句突出贴切和准确,行文极为流畅自然。”
这种自然朴实的风格也为美国新闻界所崇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新闻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甚至说:“谁只要在他的底稿上多划掉一些形容词,他的文章就会得到改进。”
其实这种写法,正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种方法——白描。白描原是中国绘画中用线条勾描物象,不着颜色的画法。借用在新闻写作中,泛指一种表现手法,即使用简笔勾勒,不加烘托,平白淡雅,以形传神地刻画出生动鲜明的形象。鲁迅曾在《作文秘诀》中对此有过解释:“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新闻语言的平淡不等于平庸和淡而无味。这里的淡是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的平白语言说出来,是富有情味的。正如诗论家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评论陶潜和谢灵运的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
《三国演义》中程普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醇醪是一种味厚的酒,上口没有刺激性,由于没有刺激性好像平淡,容易多喝,所以不觉自醉。平淡正是这样,表面平淡,含蕴深厚。
新闻中的平淡,正是这种醇醪,以平实简劲的笔触,单刀直入,虽寥寥数语,却能形意翩翩,引人遐思,回味无穷。正是:浅显中有深意,平白里寓哲理。
如一篇报道莫桑比克人民为萨莫拉总统举行葬礼的新闻,便是这样的写的——
榴弹炮鸣放二十一响礼炮,蒙着黑纱的鼓发出震响,军号吹出熄灯的号声,在萨莫拉·马谢尔总统的国葬上,送葬的人们泣不成声。
这篇新闻导语一共只有40多个字,不仅报道了葬礼的举行,还写出了送葬的情意。比起“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的空洞的叙述,这样简洁的白描可以使人体验到文字背后的深厚情感。
许多新闻名记者都在白描的表现手法上下工夫。穆青同志在《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这种表现手法,有时也借助语言的音响和色彩来加深效果,但主要依靠事实、形象、思想来打动读者。它的特点是豪华毕落见真谛,从平凡中见到深刻,在沉静中见到热烈;尽量做到自然流畅,不事雕琢。”
穆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在他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个名篇中,处处可以见到这样平白的描写: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啊!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海明威曾在堪萨斯城的明星报社工作过,即使在他离开这个报社多年后,他还对这个报社的写作规范的小册子中的规定记忆犹新。这个小册子的开篇就这样写道:“用短句子。开始的几段也要简短。运用生动的英文,不要忘记力求文字的流畅。用肯定的语气写,不要否定的。”他甚至将此作为终生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并说:“这是我学习写作中所学到的最好的规则。我从来没有忘记它们。任何一个具有才智、写他们真正感觉到的真正想说话的人,若遵守这些原则,绝不会写得不好。”
要做到有含蕴的平淡并非易事。正如王安石《题张司业》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梅圣俞在《和晏相》诗中说:“因今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后来,他在《赠杜挺之》诗中又说道:“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古人写诗已明白这个道理,内容精辟,深入浅出,好像平易,写时却要加倍用心,反复推敲,达到圆熟,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容易看,容易懂。对这种无斧凿痕的圆熟,杜甫曾有论述。他在《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中写道:“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紫燕自超出一般,说明平淡不同于平庸。名马翠驳不需要剪剔,即平淡的作品要写得看不出人工的斧凿痕迹,所以平淡又要圆熟。
含蕴的平淡,是要在平淡中含着新奇、在平淡中蕴着传神。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谈到梅圣俞的诗时说,梅诗平白浑朴中含着新意。他举了梅诗《送欧阳秀才游江西》,其起句为:“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飞,去作江西梦。”这样写春风,写客心,有新意。
路透社曾发过一个报道日本首相大平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的新闻,颇有平淡中见新奇之功。其文如下:
大平夫人看望“欢欢” “长得多么可爱啊”
“啊,新娘子,让我看看你的脸蛋吧!”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首相夫人大平志华子,七日下午访问北京动物园,看望赠送给日本的熊猫“欢欢”。
因为日本首相夫人要求参观,所以熊猫房的周围,在夫人达到前三十分钟就挤满了中国孩子。“欢欢”由屋内走到外面的运动场上,注视着这么多人,背朝着大平首相夫人,久久安静不下来。
陪同参观的邓小平副总理夫人卓琳笑容满面地说:“‘欢欢’还害羞呢!”首相夫人说:“日本人在等待‘欢欢’的到来”。可能是理解了首相夫人的话,“欢欢”终于把脸转了过来。夫人非常高兴,说:“多么可爱啊!”眯着眼睛又说:“今后务必生个小熊猫。”
(共同社北京1979年12月7日电)
这240个字的新闻,运用平白的叙述,把一场外事活动写得情趣横生,极富生活气息,似乎远远就可以听到欢笑的声音。就连“今后务必生个小熊猫”一语也颇有新意,并蕴涵深远的含义。如果按我们习惯的老路子写成“大平首相夫人大平志华子,今天下午由邓小平副总理夫人卓琳陪同,到北京动物园观赏中国人民的礼物——大熊猫‘欢欢’……希望‘欢欢’在日本传播友谊的种子”,只能是老套无味。
平白的另一个更高的境界是传神,这也是平白质朴的一个内在品格。传神指的是捉取了事物本质而产生的美学感染力,它要求透过事物内在的动态特征,表现事物的生命和神韵。运动是客观事物的共同属性,事物的本质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在新闻中写人状物,不是对事物的外在特征进行静止的繁琐的描写,更不是脱离事物特征的空泛形容。诸如“高兴地说”,“神采奕奕”之类笼统模糊的语言,不能在读者头脑中映现出生动的表象,因此不可能产生实践体验。而采用平白的叙述手法,用最少的笔墨,从动态中勾描出事物的特征,借助于读者的想象和联想活动,以感受和把握事物,便能产生神余言外的意趣。
美国《迈阿密论坛报》的记者用这种手法报道的四川说书艺人颇为传神。其文如下:
四川的说书艺人(节选)
……
在一间烟雾腾腾带有古老风味的竹椽屋子里,说书艺人钟春精神抖擞地高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边上。
他用粗犷的四川方言讲着三千年以前的故事。他用了两样世代相传的道具:一把有画的折扇和一块雕花的惊堂木。
这两样道具是为了加强书中的戏剧效果,讲到蛊惑人的妃子时用扇子,讲到凶残的皇帝时用惊堂木。在讲到故事结局时惊堂木也用来表达凛然正气。
皇帝迷恋上他的宠妃。(折扇轻摇)
皇帝和他的宠妃残酷地杀害了那位不幸的皇后。(惊堂木啪的一声!)
在东我巷的茶馆里,老人们用长长的烟杆抽着烟,从有缺口的碗里抿着浓茶,发出一声声心领神会的叹息。苦命皇后这个故事是老人们很早以前从他们爷爷口中就听到过的。他们几乎同说书人一样熟悉这个故事。然而如果不是一讲再讲,又怎能成为故事呢。
皇帝疯狂般宠爱他的妃子,把讲逆耳忠言的人投入一个蛇窖里或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剖腹挖心,(啪!)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逐出宫廷。(啪!啪!)
听书的老人们对两个王子的命运不太担心。因为这是两个健壮的小伙子。老人们都知道在下一回书中会说到他们会回来为被害的母亲报仇。
……
在这里,茶馆的浓重氛围,说书人的卖力表演,说书的传统内容,听书老人们的入迷情态,构成了一幅四川古老传统的茶馆风情画,独具地方色彩的神韵。
客观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在强调新闻写作平白质朴的同时,不可否认许多得体的浓艳风格也为人们所喜爱。这犹如绘画中的工笔技法。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画工”——刻意雕绘,细描事物的“形”;二是“化工”——精心点染事物的“神”。工笔描绘人、物、景,是将“画工”与“化工”有机结合起来,熔铸在作品之中,达到古人说的“形神兼备”。
老子曾说过:“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意思是一个表达形式的美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行为美可以让人更看重你。孔子也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两者说的都是同一意思,好的表现形式能使作品传播的空间更广阔、时间更久远。
细描和精雕往往会让事物的“形”更“浓艳”,会使作品的情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第八届中国新闻奖获得特等奖的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就是在“浓艳”中浸满了真情。
在大海中永生
——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节选)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大海的无垠,开阔了他博大的胸襟;
浪涛的汹涌,塑造了他顽强的性格。
潮起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风险,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中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
(新华社北京1997年3月2日电)
应该说,这种一波三折的精雕细刻,色彩浓重,情感细腻,将人们追念亲人之情、崇敬领袖之情、痛悼伟人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碧云天,黄花地,总是离人泪”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记者的笔下,以大海比喻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业绩和情怀,以波涛寓意他激荡沉浮的人生,以浪花负载他的理想、追求和高洁的灵魂。记者内心蕴藏的对小平同志的无比崇敬爱戴之情,和邓小平同志亲人的感情一起奔涌。
新华社副总编辑张万象指出这篇通讯有两种表现手法极为感人:其一是拟人化的抒情。“大海呜咽”那是在“痛悼伟人的离去”;天空的彩虹,那是“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而出现的;“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祖国的万里海疆”、“送向香港、澳门”、“送向台湾”……浪花能遂人意。这些拟人化的手法的抒情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正如古人悲悼时所说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二是运用诗歌反复咏叹的手法,一咏三叹。通讯中这些文学手法的运用,与通讯全篇的诗一般激越跳荡的语言、雄辩的排比、往复的对仗,使感情步步递进、升华,最后呼喊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声:邓小平——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他在大海中永生!
古人追求写景状物用工笔细描精雕,并将此作为“状难写之景如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功夫。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黛玉焚稿一节就颇见这番功夫。他写道:
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开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娟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儿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诗,挣扎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哪里撕得动?……
雪雁连忙点上灯来。黛玉瞧瞧,又闭了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紫鹃打量她冷,因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罢。那炭气只怕耽不住。”……
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她。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了点头儿,往上一撂。紫鹃唬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
黛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鹃怕她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
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
这一段描写黛玉误以为宝玉负心,便将见证她和宝玉纯真爱情的诗稿投入火盆焚了。她撕绢子和焚诗稿的动作、神态,和紫鹃、雪雁的真情体贴,使人感到作者工笔描绘手法的高超,其生动、细致,无与伦比。
在新闻写作中,平白质朴与浓重艳丽看似矛盾,但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形成统一表现事物的整体。
首先,它们统一在对事物真实的表现。平白质朴的白描意在通过简洁的笔法,以少胜多,表现事物的真实。浓艳细致的工笔,也在追求事物的细微真切,突显其多角度、多层次、多色彩、立体感强的特点。清代许印芳在《诗法萃编》中说:“……天地人物,各有情状。以天时言,一时有一时之情状;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状;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状;以物类言,一类有一类之情状。……情状不同,移步换形,有中真意。”两种表现手法,都在力求真实地描写景、物。
《他们看上去简直不成人样了》这篇原载于《纽约先驱报》的新闻曾获1946年普利策奖,也是美国新闻史上的名作之一。记者霍默·比加特细致报道了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真实的惨状:
熏黑了的光秃秃的树木残干和钢筋混凝土建筑空壳……
四处都是碎砖破瓦,但是要比正常的小得多……
数以百计的伤员无人照管……他们面部和双手烧得见了骨头,许多人眼睛瞎耳朵聋……
大街上还充溢着令人作呕的尸臭……
(《纽约先驱报》1945年9月3日)
其次,两种手法都意在通过“形似”而求“传神”。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过:“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右看不入画者,前后亦尔。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他将白描、淡彩、重彩和设骨等技法,在从形似向神似的传神中统一起来。
一些新闻大师写景中颇见传神之功。恩格斯1840年7月写过一篇通讯《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从细微之处写风光也格外传神。如写夕阳西下:
太阳宛如一个通红的火球挂在云丝织成的网上;网线仿佛已经燃烧起来了。因此时刻都可以预料:云网就要烧毁,太阳就要咝咝作响地掉进水中!
不论是平白质朴还是浓墨重彩,都是在追求自然。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质朴的白描手法,是在道法自然,力求自然圆熟。而浓艳的精雕细刻也当道法自然。离开此,便会误入歧途。宋朝的蔡梦弼在《草堂诗话》中说:“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如果华丽的辞藻脱离了真情实感、脱离了自然,就是多余的话。有内容又自然,则是情景相生的妙文。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因为绮丽自然被蘅塘退士称为“千古丽句”。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发潭州》:“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都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工笔画,又都秀丽自然。
巴金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自然为上品。正是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国门卫士——黑河好八连》中报道黑河八连的干部战士运用了声音、图画、行动等综合手段,十分自然地展示出战士爱国守边的赤子之情。该作品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如:
在八连的画展中,战士白茹学题为《母亲的思念》的素描,格外引人注目。画中,母亲独倚门前,凝神远望。其实,这不仅是母亲的期待,更是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啊!
说起母亲,战士王慧勇情不自禁。(录音):
“我对我母亲的那种感情相当深。别谈,别谈这个话题,你们换个话题!”
他家就在本省。母亲得癌症病危,他也没请假回家探望。
(录音):“冬季执勤特别忙,那个环境你们可能也来过,人特别少。我没法回家。我如果回家的话,那个岗就没法站了。这么多年来,八连冬天从来没有一个战士,一个干部回家过年。我即使心里想,也不能提这个要求。大年三十儿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站12点岗,看着过年夜的时候,街里放鞭炮特别响,我心里想我妈一定特别想我,当时我不知道妈妈已经去世了……”
战士对母亲的爱是真挚的。可为了戍边,他们把这爱深深地埋在心里。
开头这段叙述和录音,“别谈,别谈这个话题,你们换个话题!”,既有素描画的衬托,又有录音的真实记录,十分自然地刻画出了这位战士的内心世界,使报道的主题得到升华。正是“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5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