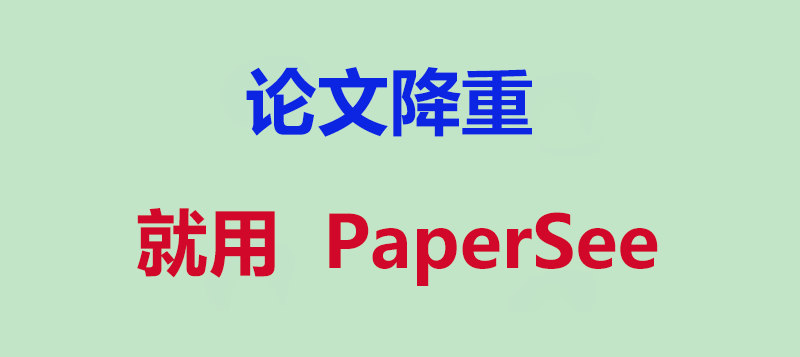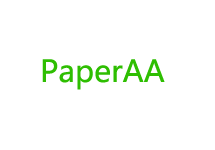一 名词背景小编:一名词背景拜伦是英国贵族、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喧嚣的文化场域中,人们高喊着语言就是力量,行动已然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当遍地都是豪
拜伦是英国贵族、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喧嚣的文化场域中,人们高喊着语言就是力量,行动已然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当遍地都是豪言壮语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到你做点什么。就像2012年7月21日北京下暴雨,所有人发微博的时候,有的人开着车拉了三四趟在路上回不了家的行人。
你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说你爱这个社会,然后当你看到老大爷伸手跟你要5毛钱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再找出一万个理由来说明他是骗子。但是,就算别人是骗子,你去证明自己善良的时候,心中收获的还是快乐。
这个时代还有理想吗?有!这个时代还有坚守理想的人吗?有!但是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坚守着理想,并付出行动的人。用鹅毛笔尽情赞美自由的大诗人拜伦,一生中最美的诗篇却不是用笔写就的。《唐璜》尚未完成,他已然从英国只身来到希腊,加入为希腊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用行动向我们诠释了真正具有震人心魄力量的诗篇,是用行动写就的。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北京大学的良心。老先生在退休之后,便到全国各地做讲座。他写过一本研究曹禺戏剧的书,叫《大小舞台之间》。在这部作品里,他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两种气(气是指风气、气味、味道)——哈姆雷特气和堂吉诃德气。
哈姆雷特是一个纠结的男人。他整天纠结在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上,但就是没行动。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虑大于一切,整天在琢磨某件事是做还是不做,他最经典的话语“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是最集中的反映。堂吉诃德,被很多人认为是精神有问题的男人。但他是行动派,没头脑。这两种人都有问题。一种全是理性没有行动,一种全是行动不用理性。所以,钱老师说这两种气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的。
在当今喧嚣的文化场域中,宁可我们有堂吉诃德气,都不要有哈姆雷特气。换句话说,宁可我们全部都是行动,少一点思虑,都不要仅仅有思虑而短了行动。小小少年没有烦恼,什么都敢做;长大了知道的事越来越多了,反而越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干了。比如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看到公交车上有人掏别人的包,你会说“妈妈,他在偷东西”。现在你一定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你担心那个小偷会对你不利。
我曾经与钱理群老师有过一次对谈,其中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国家玮(以下简称国):钱教授,您好。您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在我看来,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外到内的转变。正如您自己所说:“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那种冷漠的(人们所谓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最初与鲁迅在精神上的共鸣是如何转化成为您学术研究的动力的?民间经验和学院训练在您的鲁迅研究中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在贵州时,虽然我自以为有一个关于鲁迅的看法,但那个东西实际上是相当感性化的,后来经过学术训练以后,确实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把原来许多的感性认识大大地深化了,然后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我之鲁迅观”。
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个专业训练的话,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对鲁迅的观照;还有我非常感激北大的就是它很有学术环境,不仅是导师,还有同学,还有我后来作为教授上课接触到的那些本科的学生。当时北大整个的学术气氛是很浓厚的,在那样一个氛围下,才可能产生我的鲁迅研究。假如完全是民间的,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形态。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不分偏颇地追求这种民间的学术和学院的学术之间这种有机的结合;而我自己实际上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中国最上层和最底层、最中心和最边缘、城市和农村这样一个互动。所以我的东西有很多是来自民间的,但也有很多是学院的,因为按我的体验,这两者是可以结合的、可以互相补充的。如果只有民间经验和自己主观情感的话,它是不可能达到一定深度的,和学院的进入一个更大知识背景中的观照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民间的东西,我觉得对于鲁迅这样的对象是特别不合适的。因为鲁迅本身就生长在农村,他是民间艺术所熏陶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鲁迅和民间社会、底层社会的关系的话,你是无法去理解他的。
国:钱老师,您说到这里,引起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大概在写完研究曹禺的《大小舞台之间》后您就曾表示过要转向文学史研究,而1993年出版的《丰富的痛苦》似乎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它的切入点非常独到、敏锐,您如何看待这部著作?选定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作为参照系,这样的眼光源于怎么的思考?
钱:实际上,这是我自己最重视的几本书之一,它是我的书里面思想含量最大的一本书,它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命题,很多思考都集中在这一本书上。
当时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苏联瓦解了、东欧瓦解了,西方很多国家宣布历史终结了,有“历史终结论”;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他要逆向思维,大家都这么认为的,你要有独立的思考。
我当时就想了一个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真的就终结了吗?当时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很多时代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德国的海涅、法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鲁迅,都跟共产主义运动、跟苏联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提了一个问题,就需要研究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是什么?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这样我就把一个本来是思想政治的问题——时代主义是最重大的思想政治问题——转化成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学术课题。
而我又是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我必须把它转化成一种文学史的研究,我仍然从心灵出发,不讨论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关系的理论和思想的渊源,而是从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时候,就反过来对自己生命进行一个观照: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向往共产主义的,我们是非常积极地投入当中去的,为什么?打动了我的是什么东西?我的心灵气质中什么东西和它有吻合的地方我才去接受它,这是对自身的精神气质的反观。
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这是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连在一起的,它那种浪漫的想象、生命的激情、那种不顾后果的奋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有。还有哈姆雷特气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两类知识分子:一类具有强烈的堂吉诃德气质的常常倾向于革命;而有怀疑精神的、哈姆雷特气质很浓的知识分子常常又与革命疏离。但是也很复杂,参与到革命中具有哈姆雷特气质的知识分子仍然也有很多矛盾、有时候会产生更大的痛苦,比如何其芳就是一个典型。
当前网址:http://www.paperaa.com/news/470.html